走出 Port Authority 公車總站,穿過滴著水的工程鷹架,步上曼哈坦 (Manhattan) 街頭,迎面而來的是招手即停的黃色計程車、逆向滑行的直排輪溜冰者、以及任意穿梭的腳踏車,有人在吐痰、路旁垃圾翻飛….。眼前的一切多麼熟悉啊!這不正是我生活了半輩子的臺北嗎?我原先緊張忐忑的心情突然解放似的鬆懈下來,朋友的殷切叮嚀、旅遊書中的警語頓時全拋九霄雲外。在臺北我可以活得好好的,一定也能適應紐約!
真是「站在紐約街頭,看到都是人頭」,紐約人多車多,路人個個面無表情、步履匆匆;不小心碰觸到別人,好像也毋庸費勁說:「對不起」;"Don't Walk" 交通號誌顯然僅供參考,行人照樣不慌不忙穿越馬路;救護車卡在車陣間淒厲哀鳴,經常動彈不得。移居溫哥華後入境問俗學習多年的功夫──逢人就打起精神說 "Hello" "Sorry";中規中矩一個燈號一個動作──在此恐怕不合時宜。都會生活的另類文化又回來了!沒人睬我,我也不用理別人,這感覺真好─冷漠中自有可以獨享的一片天空。
到處高樓林立,動不動就百層以上,遊客常須趴地仰頭照相,走在其間不易曬到太陽,也難得看到日月星辰,每條大道相形之下全像小巷子。一棟棟巨廈也都失去了君臨天下或鶴立雞群的氣勢,只要隨便換個角度觀看,再高的建築均難逃被其他樓房遮蔽吞噬的命運。儘管如此,電影「金玉盟」裡帝國大廈高聳到陷進縹緲雲霧中的特寫,仍嫌誇張過頭。因為九月中至十月初的半個多月裡,我每天在紐約街頭逛,無論陰晴日夜,甚至颶風大雨,都沒機會尋找到電影中雲繞高樓的奇景。可能是拍片當時空氣污染嚴重,以致塵霧造成「雲深不知處」的病態浪漫吧!
以為時報廣場 (Times Square) 很大,至少是每年除夕夜電視新聞都要出現一次的那種人山人海的大。親臨現場時,卻產生「相見不如想念」之慨,許多事留點想像空間會好些。事實上,「時報廣場」沒有四方型空曠廣場,不是天安門也非紅場,而是類似臺北西門町的那種鬧區。只有第七大道 (7th Avenue) 與百老匯街 (Broadway) 比鄰相交而過時的路段稍為寬廣,合起來大約十線道,較有可能容納得下湊熱鬧的人群,其路邊數棟高樓上裝有大幅電視牆,上面晃動著最新廣告和時事,大概這裡就是群眾每年仰頭看螢光幕,齊聲倒數計秒歡送舊年迎接新年的地方吧。有名的百老匯音樂舞台劇場即分佈在這路段四周,經常擠滿興奮地等候進場或若有所思地出場的戲迷,入夜時五彩霓虹閃爍,招呼川流不息的過往遊客。 Duffy Square 在上述兩條大路中央,只有安全島大小,島上靠近西四十七街 (W47th Street) 的TKTS售票處經常有人排長龍買百老匯半價票;賣藝、發放廣告單、販賣飲料熱狗者絡繹不絕;也有溫哥華少見的水果攤,水果一袋袋削好裝妥靜候看戲者享用,我仔端詳卻有些失望,如果他們也賣甘草醃的芭樂或塞滿酸梅的小蕃茄就好了,西門鬧區電影街一向賣這些零食的!
買了張不限次數、七天內有效的公車地鐵兩用票,晴天時就搭公車閒逛,幾天下來,藝高膽大,逛進了哈林區。還是高樓櫛比,許多房子正面中央外牆設有防火梯,十足電影「西城故事」裡現代羅蜜歐與茱麗葉談情說愛的場景,也非常適合飛簷走壁的樑上君子使用。建築多半老舊,牆壁常見塗鴉,街頭垃圾不比他處多。居民除了黑人外,大部分為說西班牙語的中南美裔,因此,英語在哈林區常無用武之地,幸好當地人和善,迷路了照樣可以得到指點。
雨天時鑽進地鐵,迎面總是飄來一股撲鼻尿騷味,百年難消的熱氣則奮力朝頂上路面縫隙冒煙。瑪麗蓮夢露拍「七年之癢」時,站在地鐵氣孔上裙裾飛揚、巧笑倩兮的風情可能與事實有段距離,一代美女八成有苦難言,不是真的那麼興味盎然。四十二街地鐵站月台上樂聲此起彼落,有拉二胡「梅花」的老先生,也有玩小提琴兼賣自己 CD「綠島小夜曲」的臺灣人;車廂內黑人搖響裝著硬幣的紙杯,口中哼哼唱唱地向人討錢;黃臉孔的小販拉輛小菜籃車賣底片、打火機、口香糖、電池、玩具,生意很不錯。唯獨不見聲名遠播的地鐵塗鴉,聽說是新市長大力整頓的結果。
一個熱天走進中國城,大太陽曝曬著遺棄路邊的動物五臟六腑、雞頭魚尾,冒煙的地鐵氣孔蒸騰著路面斑斑血水油漬,空氣中的異味不斷膨脹,充塞在方圓數公里的領域內;人行道上塞滿小販賣食物、手錶、飾物、衣服….所有想得到或想不到的東西;水洩不通的行人則在馬路邊、車陣裡游走;警察既須揮汗維持秩序,也要忙著應付遊客問路;Pizza Hut 速食店地下室廁所煙霧迷漫,而且是少見的髒亂和簡陋,卻排了兩長隊,外加一對男女四字經高聲叫罵。據悉這是周末跳蚤市場風光。但,這是美國嗎?
不只我這異鄉人感到困惑,連外地的老美也說:「紐約不是美國」,那麼它是什麼?──聯合國嗎?
(原載 1999-12-12 世界日報家園版)
2008年6月29日 星期日
訂閱:
張貼留言 (Atom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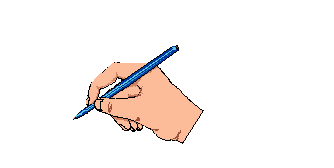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