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在列治文公共市場華人菜攤上發現久違了的絲瓜,摸著它有點風乾的表皮,一時之間,宛如他鄉遇故知,竟勾起許多回憶。
「絲瓜」臺語稱之「菜瓜」,大概是最鄉土的臺灣瓜類了(註)。
搬到嘉義不久,小弟出生了,接著新家也落成了。母親又慢慢種植出滿園花卉蔬菜。春天一來,菜瓜藤搶先以一眠大一尺的方式成長,快速地爬滿圍牆和瓜棚,葉片像張開的大巴掌層層疊疊遮掩了紅磚牆;由瓜棚下往上望,透光的葉片帶著細密的絨毛筋絡分明。捲曲的瓜鬚由葉腋伸出,牢牢纏住竹架,與瓜蔓、葉片合作無間地擴展疆土。
想到這裡,我忽然覺得葡萄藤也有極相似的模樣和生長方式,難怪當年購屋時獨鍾情現在這後院有葡萄棚的老房子!
 菜瓜花和牽牛花生命一般短暫,只一、二天就凋謝了,受粉的雌花子房慢慢膨脹,有機會長出瓜來;雄花不管有無機會傳宗接代,都難逃變成昨日黃花的命運。盛開的花趁新鮮摘下,可以裹上麵粉蛋液,炸成香酥的美食;在那生活簡單的年代裡,這菜頗受小孩歡迎呢。
菜瓜花和牽牛花生命一般短暫,只一、二天就凋謝了,受粉的雌花子房慢慢膨脹,有機會長出瓜來;雄花不管有無機會傳宗接代,都難逃變成昨日黃花的命運。盛開的花趁新鮮摘下,可以裹上麵粉蛋液,炸成香酥的美食;在那生活簡單的年代裡,這菜頗受小孩歡迎呢。
 那時,院子種的通常是竹竿種或長筒種,成熟的圓筒形菜瓜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分,直徑約八、九公分;後來,瓜肉細嫩、果實長約二十公分的米管種在市場上漸漸取代了其他品種,筒身粗細卻還一樣,看起來矮矮胖胖。菜瓜綠色外皮疙疙瘩瘩地,瓜身分佈西瓜般的細縱紋。和挑選其他蔬菜的訣竅相似,選菜瓜也有個祕訣──拿在手上感覺越重、縱紋刻度越淺者越新鮮;嫩瓜外皮疙瘩較粗糙,甚至帶點灰色果粉,摸起來堅實飽滿。
那時,院子種的通常是竹竿種或長筒種,成熟的圓筒形菜瓜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分,直徑約八、九公分;後來,瓜肉細嫩、果實長約二十公分的米管種在市場上漸漸取代了其他品種,筒身粗細卻還一樣,看起來矮矮胖胖。菜瓜綠色外皮疙疙瘩瘩地,瓜身分佈西瓜般的細縱紋。和挑選其他蔬菜的訣竅相似,選菜瓜也有個祕訣──拿在手上感覺越重、縱紋刻度越淺者越新鮮;嫩瓜外皮疙瘩較粗糙,甚至帶點灰色果粉,摸起來堅實飽滿。
從前,尚未有電鍋、瓦斯爐的年代,清理被柴火、煤炭燻黑或油膩沾粘的鍋碗瓢盆是主婦餐後的苦差事。那時沒什麼塑膠或化學清潔用品,一般人都利用家裡自產的絲瓜絡橫切成容易掌握的大小,沾著炭灰、煤灰來洗刷鍋底。
臺語稱絲瓜絡為「菜瓜布」,即纖維變粗、剝去外皮、倒出比西瓜子略大的眾多成熟黑種子後的老瓜殘骸。這些廚房好幫手通常都是菜瓜盛產後的副產品,因一整夏吃不完,於是任其自然老化,直隨一年生老株同枯於冬季。採收時,蔓藤仍緊緊拉住原瓜,瓜形沒變,咖啡色外皮卻常已殘破易碎,瓜肉不存,僅剩縱橫交錯、牢牢密織的纖維化菜瓜布。現代人用的人造菜瓜布質感用途均仿自天然菜瓜布,但,天然的是黃褐色、纖維空隙較大且不均勻。
有次參觀亞特蘭大歷史博物館保存的十九世紀莊園,赫然發現如假包換的天然菜瓜布。美國南方也生長菜瓜嗎?他們廚房居然少不了菜瓜布哩!那感覺真親切。如果溫哥華也能看到隨處攀爬的菜瓜藤就更完美了,對不對?
(原載2000/6/10世界日報家園版)
※註:
據王禮陽著 "台灣果菜誌" 記載:菜瓜傳自印度,原稱蠻瓜,移臺先民把蠻瓜一併攜至台灣,因不願有身在蠻荒的聯想,而絲瓜又可入菜,故改名為「菜瓜」。
台灣的菜瓜分成三種:普通絲瓜、細長絲瓜(蛇瓜)、稜角絲瓜(澎湖菜瓜)。一般人及本文說的「菜瓜」是普通絲瓜。
有首童詩相當傳神:『三月裡種絲瓜,四月瓜藤滿牆爬,五月裡開黃花,六月結個大絲瓜,風兒吹瓜落下,打著院子裡的小娃娃,娃娃哭,罵絲瓜,絲瓜說:「罵風,別罵咱!」』只是,我看過風起果落的芒果,卻從來沒見過風一吹就落地的絲瓜。印象中纖維粗韌的瓜蔓總盡責地拉住下垂的絲瓜,成熟的瓜除非用刀割斷,照說應該很難取下才對。而且,天氣較熱的屏東等地在四月就有當令的新鮮瓜可吃了,不一定要等到六月。
三、四十年前,“公寓”這東西仍很少見,一般住家院子幾乎必種菜瓜。有則故事提及菜瓜的普受歡迎:有個媽媽高高興興去兒女家做客,吃飯時間到了,老大沒留她一起用餐,老二也無意邀她,老三家徒四壁有心無力,老媽媽只得長嘆一聲:「還不如家裡的菜瓜!」然後摸摸鼻子落寞返家吃自己去了。
「絲瓜」臺語稱之「菜瓜」,大概是最鄉土的臺灣瓜類了(註)。
最早認識「菜瓜」這東西是五歲某個夏日早上。那天曉霧未散,陽光若有若無地伸著懶腰,隔夜的露珠依舊垂掛葉尖晶瑩發亮,空氣中帶著清晨溫潤的青草味,新的一天才剛緩緩甦醒。當時我站在家門口,望著大人忙進忙出將打包好的家當全搬進大卡車裡,我們原本就庭院深深、光線不足的日式宿舍,這下更顯現出被掏光後的空蕩森冷,涼風夾著輕紗般的霧氣穿堂過室,佔據了屋內每一角落。等一切就緒,搬家車隊正待啟動時,身懷六甲的母親回身從牆邊切斷的老藤取下盛滿菜瓜水的玻璃瓶,然後我們登車揮別那住了三、四年有大片甘蔗田、玉米田、花生田的臺南農業改良場宿舍,一路小心翼翼捧著瓜液回到嘉義故鄉。而那壯烈犧牲的粗瓜藤就此定格在我越老越鮮明的記憶裡。
那瓶子裝著清涼退火、養顏美容的菜瓜水,也裝著母親離開經營多年家園的不捨。對我而言,那兒有人生最初的記憶,我清楚地記得許多曾發生的片段。
搬到嘉義不久,小弟出生了,接著新家也落成了。母親又慢慢種植出滿園花卉蔬菜。春天一來,菜瓜藤搶先以一眠大一尺的方式成長,快速地爬滿圍牆和瓜棚,葉片像張開的大巴掌層層疊疊遮掩了紅磚牆;由瓜棚下往上望,透光的葉片帶著細密的絨毛筋絡分明。捲曲的瓜鬚由葉腋伸出,牢牢纏住竹架,與瓜蔓、葉片合作無間地擴展疆土。
想到這裡,我忽然覺得葡萄藤也有極相似的模樣和生長方式,難怪當年購屋時獨鍾情現在這後院有葡萄棚的老房子!
 菜瓜花和牽牛花生命一般短暫,只一、二天就凋謝了,受粉的雌花子房慢慢膨脹,有機會長出瓜來;雄花不管有無機會傳宗接代,都難逃變成昨日黃花的命運。盛開的花趁新鮮摘下,可以裹上麵粉蛋液,炸成香酥的美食;在那生活簡單的年代裡,這菜頗受小孩歡迎呢。
菜瓜花和牽牛花生命一般短暫,只一、二天就凋謝了,受粉的雌花子房慢慢膨脹,有機會長出瓜來;雄花不管有無機會傳宗接代,都難逃變成昨日黃花的命運。盛開的花趁新鮮摘下,可以裹上麵粉蛋液,炸成香酥的美食;在那生活簡單的年代裡,這菜頗受小孩歡迎呢。 那時,院子種的通常是竹竿種或長筒種,成熟的圓筒形菜瓜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分,直徑約八、九公分;後來,瓜肉細嫩、果實長約二十公分的米管種在市場上漸漸取代了其他品種,筒身粗細卻還一樣,看起來矮矮胖胖。菜瓜綠色外皮疙疙瘩瘩地,瓜身分佈西瓜般的細縱紋。和挑選其他蔬菜的訣竅相似,選菜瓜也有個祕訣──拿在手上感覺越重、縱紋刻度越淺者越新鮮;嫩瓜外皮疙瘩較粗糙,甚至帶點灰色果粉,摸起來堅實飽滿。
那時,院子種的通常是竹竿種或長筒種,成熟的圓筒形菜瓜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分,直徑約八、九公分;後來,瓜肉細嫩、果實長約二十公分的米管種在市場上漸漸取代了其他品種,筒身粗細卻還一樣,看起來矮矮胖胖。菜瓜綠色外皮疙疙瘩瘩地,瓜身分佈西瓜般的細縱紋。和挑選其他蔬菜的訣竅相似,選菜瓜也有個祕訣──拿在手上感覺越重、縱紋刻度越淺者越新鮮;嫩瓜外皮疙瘩較粗糙,甚至帶點灰色果粉,摸起來堅實飽滿。
菜瓜的家常煮法多半爆香紅蔥頭或薑絲來清炒去皮的切片瓜肉,有時再加點肉類、蝦米煮成鹹稀飯。炎炎夏日裡,軟甜、多汁、清淡、白肉白子鑲著綠邊的菜瓜是許多家庭常見的桌上菜,也是百吃不厭、袪暑消熱的美食,那裡面有令人深存心頭的媽媽的味道。
從前,尚未有電鍋、瓦斯爐的年代,清理被柴火、煤炭燻黑或油膩沾粘的鍋碗瓢盆是主婦餐後的苦差事。那時沒什麼塑膠或化學清潔用品,一般人都利用家裡自產的絲瓜絡橫切成容易掌握的大小,沾著炭灰、煤灰來洗刷鍋底。
臺語稱絲瓜絡為「菜瓜布」,即纖維變粗、剝去外皮、倒出比西瓜子略大的眾多成熟黑種子後的老瓜殘骸。這些廚房好幫手通常都是菜瓜盛產後的副產品,因一整夏吃不完,於是任其自然老化,直隨一年生老株同枯於冬季。採收時,蔓藤仍緊緊拉住原瓜,瓜形沒變,咖啡色外皮卻常已殘破易碎,瓜肉不存,僅剩縱橫交錯、牢牢密織的纖維化菜瓜布。現代人用的人造菜瓜布質感用途均仿自天然菜瓜布,但,天然的是黃褐色、纖維空隙較大且不均勻。
有次參觀亞特蘭大歷史博物館保存的十九世紀莊園,赫然發現如假包換的天然菜瓜布。美國南方也生長菜瓜嗎?他們廚房居然少不了菜瓜布哩!那感覺真親切。如果溫哥華也能看到隨處攀爬的菜瓜藤就更完美了,對不對?
(原載2000/6/10世界日報家園版)
※註:
據王禮陽著 "台灣果菜誌" 記載:菜瓜傳自印度,原稱蠻瓜,移臺先民把蠻瓜一併攜至台灣,因不願有身在蠻荒的聯想,而絲瓜又可入菜,故改名為「菜瓜」。
台灣的菜瓜分成三種:普通絲瓜、細長絲瓜(蛇瓜)、稜角絲瓜(澎湖菜瓜)。一般人及本文說的「菜瓜」是普通絲瓜。
有首童詩相當傳神:『三月裡種絲瓜,四月瓜藤滿牆爬,五月裡開黃花,六月結個大絲瓜,風兒吹瓜落下,打著院子裡的小娃娃,娃娃哭,罵絲瓜,絲瓜說:「罵風,別罵咱!」』只是,我看過風起果落的芒果,卻從來沒見過風一吹就落地的絲瓜。印象中纖維粗韌的瓜蔓總盡責地拉住下垂的絲瓜,成熟的瓜除非用刀割斷,照說應該很難取下才對。而且,天氣較熱的屏東等地在四月就有當令的新鮮瓜可吃了,不一定要等到六月。
三、四十年前,“公寓”這東西仍很少見,一般住家院子幾乎必種菜瓜。有則故事提及菜瓜的普受歡迎:有個媽媽高高興興去兒女家做客,吃飯時間到了,老大沒留她一起用餐,老二也無意邀她,老三家徒四壁有心無力,老媽媽只得長嘆一聲:「還不如家裡的菜瓜!」然後摸摸鼻子落寞返家吃自己去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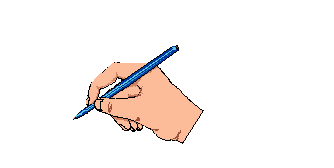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